公众号:白星澜
季节倒流的劳作
到达葡萄园的那个黄昏,天空正铺展着一片我从未见过的紫色——不是槟城海岸日落时那种掺了金粉的绯紫,而是内陆才有的、熟透到近乎墨黑的浓紫。南半球的二月,马来半岛的雨季应该还未收梢,空气里满是榴莲熟裂的暖腻;这里的风却干燥粗粝,带着桉树挥发的辛辣。农场主约翰是个红脸膛的汉子,手掌阔大,握上去时能感到坚硬的茧子。他指了指山坡下那片灰铁皮屋顶的工棚:“你们住那儿。明早五点,太阳还没把露水舔干的时候,就得开始剪枝了。”
我的“邻居”们,是几张同样被赤道阳光吻过的面孔,却说着不同质地的话语。阿明来自吉打州,和我一样是马来西亚华人,开口是掺杂了闽南语尾音的马来式华语;台北来的雅婷,嗓音糯软,每个句子都像裹着珍珠奶茶里的粉圆;香港仔阿杰说话节奏快如电车叮当,粤语里夹杂着利落的英语单词;还有河北的大伟,一口卷舌音厚实得像北方的黄土。我们这群散落南半球的“中文使用者”,在葡萄藤间重新拼接起一片移动的、微型的故土版图。
真正的劳作开始于某个尚未完全醒来的清晨。露水沉甸甸地压在葡萄叶上,一碰,就凉丝丝地碎在手腕。我学着大伟的样子——他是我们中唯一有过北方农田经验的——左手轻轻拢住一串“西拉”,右手将弯月形的剪刀凑近果梗。这动作看似简单,却藏着分寸。最初的几串,我笨拙得很。汁液黏稠,很快就在指缝间结成深紫色的糖痂,混着尘土的微粒,渗进掌纹里。
“喂,不是这样啦,”阿杰凑过来,用他修长的手指示范,“手腕转一下,像拆凤爪关节那样,轻巧的嘛。”他比喻得奇怪,手势却精准。
雅婷在旁边轻笑:“我们那边讲,要像捡红豆一样,一粒一粒心思。”她剪下的果串,梗口整齐得宛如艺术品。
阿明抹了把汗,用马来语嘟囔了一句:“Lama-lama jadi ala(慢慢就习惯了)。”这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切换键,当疲惫淹没时,母语的碎片便浮上来,像海面上的椰子壳。
太阳升高了。热量不再是抽象的词汇,它有了重量和质感。偶尔直起身,世界会在瞬间眩晕成一片白茫茫的光海。时间变得粘滞,只有剪刀开合的“喀嚓”声,单调而固执地,将漫长的白昼切割成一小段、一小段的重复。在这重复中,口音的壁垒渐渐被汗水蚀穿。大伟说起他河北老家冬天窖藏的大白菜,阿杰怀念深水埗排档的酥脆炸大肠,雅婷描述阳明山夜晚的硫磺气息,而我和阿明,则争辩着槟城炒粿条与新加坡黑椒蟹究竟谁更能代表“南洋味”。食物是故乡最忠实的信徒,在异国的烈日下,我们用语言烹煮一道道消失的盛宴,喂饱思乡的胃。
中午,我们躲到几棵尤加利树稀疏的影子里。树皮斑驳脱落,散发着一种清冽的、类似薄荷与樟脑混合的香气。雅婷拿出她的宝贝——一只小陶壶,泡起冻顶乌龙,茶香幽然,与周遭粗犷的环境奇异地和解。阿杰分享他从香港带来的陈皮姜,酸甜辛辣,提神醒脑。大伟啃着像石头一样坚实的北方馍片,我和阿明则分享着包里最后一点肉干,那是来自热带阳光的浓缩滋味。我们很少谈论宏大事物,只是在这些细微的分享中,确认彼此身上那片共同海域吹来的风。
寂静并非真空。当身体的躁动沉淀下去,另一种更丰饶的声响世界便浮现出来。风掠过成排葡萄藤的尖梢,是持续的、潮水般的沙沙声。最大的声响,竟是寂静本身——一种蓬松的、充满弹性的寂静,将劳作时粗重的呼吸、剪刀的金属咬合、甚至心跳,都温柔地包裹、吸纳。在这广漠的寂静里,偶尔飘来几句零散的对白,像寂静湖面跃起的鱼:
“你看这云,像不像阿里山上的?”
“更似维港个日落咯。”
“俺觉得像华北平原收麦子时,天边那卷云。”
“Macam langit di kampung(像家乡的天空)。”
同一片天空,在我们眼中折射出无数个故乡的轮廓。
劳动是身体与这片南半球土地最直接的对话。几天后,酸痛从表层肌肉潜入更深的骨头缝里。但奇异的是,一种新的韵律也在疼痛中诞生。我不再需要刻意寻找果梗的位置,手指在密实的叶蔓间探入,便能准确地触摸到那一小段需要切割的坚硬。剪刀的张合成了手臂的延伸,节奏与呼吸同步。我开始辨认每一株葡萄藤微妙的脾气。汗水不再只是负累,当一阵难得的凉风穿过汗湿的后背,那瞬间的激灵,竟成了劳作中隐秘的奖赏。皮肤被晒成了熟麦色,与这里的土地、藤蔓的颜色渐渐趋同。
然而,身体的驯服与融入,并未完全消弭心底那丝游移的陌生。那陌生感在夜深人静时最为清晰。工棚的窗户没有窗帘,南十字星冷冽的清辉毫无阻碍地泼洒进来。躺在狭窄的床铺上,耳朵里还回响着白日的蝉鸣,意识却时常恍惚。某个剪枝的瞬间,指尖传来葡萄果实的凉意,我会突然想起金马仑高原的草莓,也是这般饱满,却生长在永恒的春天气息里。又或者,傍晚收工时,望见天边火烧云将葡萄园染成一片壮丽的血红,阿杰会脱口而出:“哇,像狮子山浴血。”雅婷则轻声说:“这红,让我想起九份的灯笼。”大伟沉默看着,半晌说:“跟俺们那儿的高粱晒红了脸,一个样。”同一片晚霞,在我们眼底燃烧出不同的乡愁光谱。我成了一个季节与记忆的混血体,在南半球的盛夏,体内同时流淌着北半球故土的寒冬、赤道终年的炎夏,以及所有同伴们带来的、四季错位的乡愁。我们是一群用身体丈量地球时差的人。
葡萄的成熟是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。果肉日益丰腴,将外皮撑得紧绷透亮。空气里的甜香也日渐浓郁,发酵般带着醇厚的诱惑。这变化是缓慢的,却又在某个时刻显得猝不及防。
农场主约翰巡看的次数频繁起来。他会随机掐下一颗葡萄,用粗大的手指捻破,观察汁液的色泽,或者直接丢进嘴里,眯起眼睛,用全部的感官去品评。他的表情就是我们的晴雨表。某天,他嚼着一颗“赤霞珠”,眉头先是一紧,随即舒展,眼中闪过一道光,对工头点了点头。消息像野火传遍葡萄园:收获季,要提前开始了。
空气骤然绷紧。新的工具被分发下来,是更小巧锋利的弧形果刀。休息时的闲谈少了,大家默默擦拭刀具,检查箩筐的系带。一种混合着疲惫与兴奋的紧张情绪,在沉默的工棚里弥漫。雅婷小心翼翼地包好她的茶具,阿杰检查他随身听的电池,大伟将家人照片塞进枕头更深处,我和阿明对视一眼,用一句古老的马来谚语互相打气:“Hujan emas di negeri orang, hujan batu di negeri sendiri, baik lagi di negeri sendiri(他乡金雨,不如故乡石雨)。”但我们都清楚,我们正是为了见识那“金雨”,才漂泊至此。
第一串被正式剪下的葡萄,在晨光中沉甸甸地坠入我手中的塑料筐。果霜莹莹,折射着微光。我忽然想起昨夜临睡前,大家难得的集体沉默。后来阿明轻声说,他想起祖母在橡胶林割胶的样子,也是这般黎明前的黑暗中开始,胶汁如奶白的泪。雅婷说,她母亲在茶园采一心二叶,指尖染着终年不褪的绿。大伟说起父亲在麦田弯腰挥镰,脊背弯成一座山的剪影。阿杰则回忆童年跟父亲上茶楼,看见老师傅用精巧的钳子料理虾饺。所有的劳作,所有的离乡背井,所有的技艺与传承,最终似乎都凝结于这最原始的动作——用双手向土地索取甜蜜,在异乡复刻父辈的姿势。剪刀是我父亲的割胶刀,是雅婷母亲的采茶指,是大伟父亲的镰刀,是阿杰眼中茶楼师傅的银钳。我们切割的,不仅是果梗,也是我们与各自源头之间,那看不见的、坚韧的脐带。
箩筐渐满,被抬上小型拖拉机,运往山坡下的酿造厂。我们继续在藤蔓间移动,身后留下被“掠夺”一空的安静枝桠。手臂机械地重复着动作。这些葡萄,最终会成为贴上标签、陈列在遥远国度商场货架上的葡萄酒。或许某一天,在台北的茶艺馆,香港的大排档,河北的农家炕头,或槟城的茶室,有人会啜饮一杯由这片共同劳作过的阳光、雨水与汗水酿成的液体。他们品尝到黑莓的香气、胡椒的辛感,或是橡木桶的烟熏味,但他们不会尝出其中那复杂的、属于所有中文乡愁的涩——那里面有华北平原的尘土,有维多利亚港的海盐,有阳明山的雾气,也有赤道终年不散的溽热。那将是我们存在过的、最隐晦的证明,是一封寄往所有故土方向、却无人能完整签收的家书。
终于,最后一片葡萄园被清理完毕。巨大的榨汁机在厂房里开始轰鸣。结工资那天,约翰给了每人一小瓶当年的新酒,粗糙的玻璃瓶上贴着简易标签。他用力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,用他学会的唯一一句中文说:“谢谢。辛苦了。”
离开的早晨,我起得很早,独自走到最近的山坡上。葡萄园在晨曦中一片静谧,失去了累累果实的藤蔓显得瘦削而安详。身后传来收拾行囊的细碎声响,阿杰在轻声哼着粤语老歌,雅婷的茶壶轻轻碰撞,大伟厚重的行李包拉链划过空气,阿明用马来语低声计数着最后的澳元。
我们没有说再见。就像那些被剪下的葡萄,终将奔赴不同的橡木桶,经历各自的发酵与陈年。但我知道,在某个未来,当我在吉隆坡湿热的夜晚,雅婷在台北微凉的街角,阿杰在香港拥挤的地铁,大伟在河北辽阔的平原,我们仰头饮下任何一杯深红色液体时,舌尖都会莫名记起——那一年,南半球天空下,共同熟透的紫色,与指缝间怎么也洗不掉的、甜而微涩的乡愁。那味道,会在记忆里继续发酵,愈久,愈醇。
支持作者
喜欢这个作品?请略表心意。
发布于 2026-01-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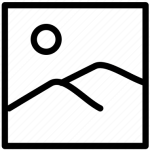
1 comment
写得真好呀!
让读者从你的经历中,
一窥打工度假者,远赴他乡在葡萄园里辛勤工作的实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