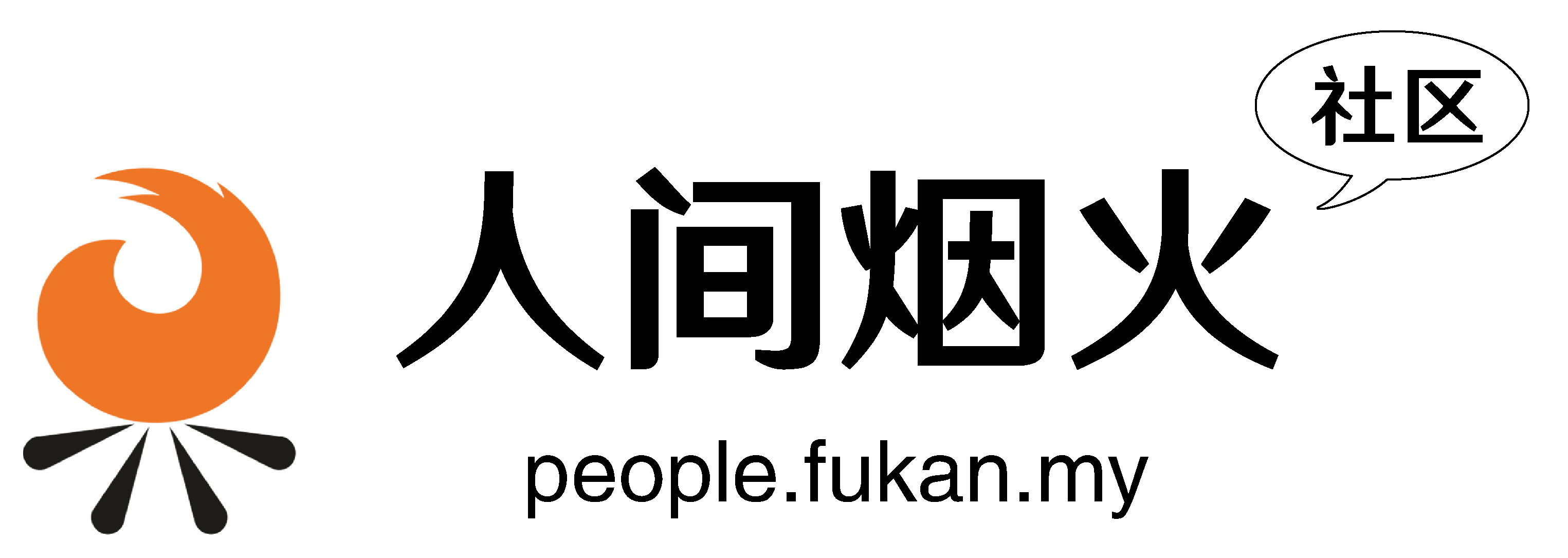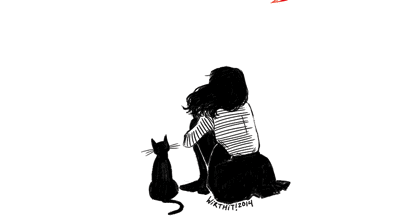公众号:心棲
這⼀步,
是恐懼推著我走?還是愛牽著我前⾏?
我們總以為,⾏動來⾃⾃由意志,
以為選擇是⼀種光明正⼤的決定。
但其,許多時候,
我們只是順從了⼀種內在的召喚——
不是理智,⽽是⼀種情緒的殘影,
⼀段未竟之事的回聲。
我們以為⾃⼰在選擇,
但若從未回頭凝視,
那些腳步,其只是重複。
在命運的長河中,
我們反覆演著⼀場劇,
⽽劇本,往往只由兩個⾓⾊執筆:
恐懼,或愛。
恐懼,是個偽裝⼤師。
它不總是驚慌失措的模樣,
有時,它穿上掌控的外衣;
有時,它藏在靜裡,像⼀⼝未曾開啟的井;
有時,它甚⾄假扮成受傷的⼩孩,在⾓落靜靜哭泣。
我們怕被拒絕,怕再次孤單,
怕沒⼈理解我們⼼底那⼀塊柔軟未癒的傷,
怕愛⼀次,便再也無法承受失去。
於是,我們變得鋒利。
先發制⼈,以強悍遮掩脆弱;
我們把「應該」掛在唇邊,把「別⼈怎麼看」當成鎧甲;
我們讓⾏為走在情感之前,只為了避免那熟悉的痛感,重來⼀次。
但恐懼也曾是守護者。
它讓我們在暴風雨中縮⾝求存,
讓我們在語⾔未及之處,先學會如何避開傷害。
恐懼不是錯,它只是還未學會安放的疼痛。
我曾陪伴過⼀位男孩。
他總是在愛裡拼命努⼒,事無巨細地照顧對⽅、理解對⽅,
但當關係稍微進入平穩,他便陷入莫名的不安。
他說,他害怕——
不是怕被離開,⽽是怕⼀切太好,以致無法承受失去的可能。
於是他過度付出,過度控制,直到對⽅漸漸無法呼吸。
後來他終於明⽩,他不是在愛對⽅,
他是在安撫⾃⼰內在那個,被拋下過的孩⼦。
榮格說:
「除非你讓無意識變得有意識,否則它將主宰你的⼀⽣,⽽你會稱之為命運。」
我們以為⾃⼰在掌舵,
卻不知多數的決定,早在語⾔成形之前,已潛伏在⼼底。
那些起⼼動念,不只是個⼈的創傷,
它們來⾃⽂化的河流、來⾃世代的陰影,
像風⼀樣穿過我們,留下集體記憶的味道。
在東⽅世界,愛經常被等同為犧牲。
我們的語⾔裡有太多關於「為你好」、「要忍耐」、「要懂事」的祕密教條。
「犧牲才是愛」、「脆弱是不對的」、「要被需要才有價值」——
這些無聲的信念,早在我們學會說第⼀句話時,便已悄悄落座。我們以為我們在愛,
其是害怕不被愛;
我們以為我們在給,
其是害怕沒有價值。
但愛,從來不是交換。
它是⼀種無需證明的存在。
它不喧嘩,也不急著解釋,
它像深⼭湖泊,在靜默中擁有⾃⼰完整的宇宙。
當⼀個⼈出於愛,他不再需要誰對誰錯,
他願意放⼿,也願意等待;
他能在失去中保有信任,
在⿊暗裡仍望⾒光的⽅向。
愛,是無劇本的⾏動。
它不來⾃習慣的回應,⽽來⾃當下那⼀刻最真的⾃⼰。
是經過內在對話後,誕下的選擇。
真正的⾃由,不是「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」,
⽽是「我知道⾃⼰為什麼這麼做」。
那是⼀種穿越的勇氣。
你開始能察覺:
「這個反應,是出於恐懼啊。」
「我⼜走回那條熟悉的防衛路線了。」
在神經科學中,這樣的⾃我察覺是前額葉⽪質與杏仁核之間的對話。
杏仁核掌管恐懼與求⽣本能,它讓我們在過去的創傷中「快速反應」;⽽前額葉,則
是調節、思考、選擇的中樞——讓我們「有選擇地回應」。每⼀次的「停下腳步」與⾃我反思,就是在強化⼤腦的覺察通路,重建情緒的掌控
⼒。
那⼀刻,你不是在重複,
你是在重寫。
這樣的覺察,便是療癒的開端。
是⼀道縫隙透進的晨光,
是⼀⾴靈魂,輕輕翻動的聲⾳。
在下⼀次你感到焦慮、煩躁、委屈時,暫停五秒。
不急著反應,先在⼼裡輕聲問⾃⼰:「我現在是在怕什麼?」、「這個反應,是我熟
悉的嗎?」
然後,⽤紙筆寫下:「如果這份情緒會說話,它想對我說什麼?」
書寫本⾝,就是在將情緒交給前額葉處理,讓⼤腦從「反射」轉向「選擇」。
恐懼讓我們活下來,
愛讓我們活出來。
我們的每個選擇,不只是⾏為的結果,
它們是來⾃內在深處的回聲——
來⾃童年的某個凝視、祖輩未竟的願望,
甚⾄來⾃整個⼈類靈魂,跨越時間的渴望與回⾳。
在我們早期的親⼦關係中,如果愛是不穩定的、條件式的,那我們的⼤腦會學會「⽤
表現換取愛」的模式,這就會延伸為成⼈後的依附焦慮、討好傾向或過度獨立。
療癒的⽅法,並不是否定⾃⼰過去的防衛,⽽是在當下與⾃⼰重建新的關係。
這個過程,⼼理學稱為「重塑內在依附圖譜」。你可以在每⽇睡前,閉上眼,想像你內在那個受傷的⼩孩,輕聲對他說:「我在這
裡,我聽⾒你了。你現在安全了。」
每天⼀點點,就夠了。
願我們學會辨識這些聲⾳。
在每⼀個即將重複的瞬間,
靜靜停下腳步,問⾃⼰:
「這⼀步,
是恐懼推著我走?
還是愛牽著我前⾏?」
发布:2025-03-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