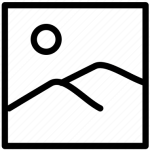公众号:温水
借自己不久前刊登于星洲日报的这篇散文来谈谈这个名为“别扭”的复杂情绪。
初次习字,是母亲教我如何写自己名字的笔画。我两手各抓一支笔,笔杆很重,比手大出许多。
母亲说左手写字好,用左手的小孩聪明;又说右手也罢,右手写得省力。若是二选一,就一定要
放弃一方吗?于是我把笔握得更紧。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大名——郑睿婷,却对它生
不出欢喜。郑的耳朵不能画太圆,睿到底有几撇?由于总是困在前两个字里,最后轻松写出的婷
倒是平淡了去。即使适应了万事开头难,想学会左手握笔的那口气却没松下去。母亲说大部分人
都是这样的,和大家一样没关系。是吗,若是知道往后压根无人在意握笔的是哪只手;或是早料
到有一天只需敲键盘…
”好难写“这是我对自己名字的初印象。从孩童时期的懵懂无知到初次步入构建自我的阶段,实在是一关比一关难。断奶、吃辅食、牙牙学语、写字、认字、换牙都是每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过程。此刻回望是不觉得难了,甚至有些情绪显得很多余。(就如网络上常讲的:人甚至不能共情从前的自己。)可真实经历过“难”的心情,才让我们得以走到这一步。(回头看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)我认为情绪就像肌肉,经历得越多才越结实。
在我们的国家,无论如何都得要三种语言打底。某一天母亲就如上了自动发条般开始一句话换三
种语言重复地说,她说有基础才不难看懂教材。我不明所以地盯着冰箱里的炼乳罐——五官立体
的女人,头上顶着一个牛奶桶。那张白底蓝字的画卷点缀一点点醒目的红,写着什么,我看不懂。
每当问母亲这个问题,她总是连珠炮地重复“牛奶,milk,susu…”我知道那是指罐子里头的米色
甜浆,稀释后是较甜的牛奶,也可以直接涂在面包上。只是她头顶的牛奶桶,身边巨大的咖啡杯
是哪里的地标?是不是和母亲的娘家一样远… “妈妈,cap junjung 是什么意思?”她见我模仿画中女
郎般将炼乳罐子顶在头上,依旧重复着死记硬背的强行适应。
相信母语为中文的马来西亚华人不难理解,为了读懂课本、考取好成绩、得到立足的资本,不得不舍弃一点母语上的深度交流。我的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实用主义者”,会为生活中的必要因素做足准备。但反复辗转的三语,通常只讲了一句最浅白的话… 我们的沟通进度条就这样常常止步不前。大马人熟知的cap junjung牌炼乳,背后有许多很有意思的故事。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21年4月1日在“面对消费者受教育不高 早期炼奶的中文名策略”的文章中,就书写了牛奶译名同当时人名教育水平之间的发展关系。
小学入学第一天,班上好多男同学因为想家掉了眼泪。实际家离学校没几公里远… 想起母亲的娘
家驱车半小时的距离,离开好几年也不见这女孩哭。它同样也在这片长满三角梅的沃土,这个答案
来自她的梳妆台抽屉里的一张老照片。因为实木材质结结实实;也因它是妈妈其中一套嫁妆,以
至我如今仍然记得抽屉拉开的重量。那是她比当时还要年轻几分的脸,怀里抱着零岁的女婴。当
时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,也能无师自通地认出自己。她身后紫色的三角梅,比家门前看惯了
的枚红色新奇点。那一刻,我好像发现了:神态轻松的挤奶女工;抱着婴儿的母亲,都透出了陌
生的别扭。
我很少从母亲口中了解到她过去的生活,只能通过一些实体化的线索慢慢拼凑,猜想。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都开着三角梅,有时到西马一段时间会很想家,可其实家也不远,至少还看得见三角梅。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,离家不远也会难过。
看着茶餐室的菜单,知晓奶茶是茶粉兑淡奶冲泡的,生熟蛋并非可生食的无菌蛋。“淡奶喝多了对
身体不好”男友如此劝戒我。我蹙眉说自己知道,又气不过地补上“你也少吃生熟蛋!”西马半岛的
天比我家晚一个小时左右黑,吉隆坡的高楼比土生土长的三角梅还像本地人。我问男友:“将来结
婚了,我就是吴太太了吗?”他回答称是。我又接着问“那你呢?你是郑先生吗?”一千多公里外的
夕阳和紫红色的花,还有我艰难学会书写的姓氏,又使我问出这种别扭的问题。
生活似乎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。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“难关”地成长起来,可在女孩子克服学写姓名的“难”到离开家的“难”,再到为人妻子的“难”,再到成为一个母亲之后的自然而然。都透出一种对“难”避而不谈的别扭。比起这种不完整的“轻松”;或理应如此的生活。我更想从真实的“别扭”中,读到完整的真实——后殖民社会中文化交杂的普遍困境:文化归属、身份认同、性别规范的夹缝中,个体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?
别扭,也是构建自我的过程中,不可或却的一步。
《别扭》——郑睿婷/刊登于2025年5月22日,星洲日报副刊(文艺春秋)。
支持作者
喜欢这个作品?请略表心意。
发布于 2025-05-26